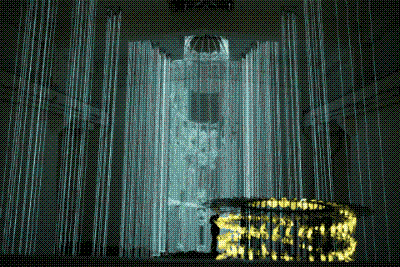2016.04.09 - 05.08
新闻稿
策展人文章
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糟糕的年代;这是智慧的年头,这是愚昧的年头;这是信仰的时期,这是怀疑的时期;这是光明的季节,这是黑暗的季节;这是希望之春,这是失望之冬;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,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;我们正走向天堂,我们也直下地狱。
----节选自 查尔斯.狄更斯《双城记》
1968年,库布里克公映了科幻电影《2001太空漫游》,电影中,人猿在狂喜时抛起骨头,画面一转,变幻成太空中悠然漫步的宇宙飞船。它带给那个时代的人们,极大的时空震撼,几万年间,弹指一挥的波澜壮阔与豪迈情怀。同年,南非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,希莱贝尔格成为第一个因心脏移植手术,而获得新生的人。
远在万里外,古老的藏族人,依旧每年会在特殊的节日,举行一种叫“转山”的宗教仪式,意为朝圣冥想之行。朝圣者花上数天,围绕圣山行走、冥想、祈祷,期望空无于永世极乐的状态。
历史上许多时刻或是古老的仪式,在斗转的时空中,总会被染上天启般的色彩。事后回想,总带有悲剧式的美感,成为一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,激发着后人的诸多想象。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的丰富起来,原本茫然无措的心境,也开始被一种叙事的浪漫所带动,距离变的浓稠有味。2006年,许仲敏创作了一件名为《转山》的机械装置,寄予个人的对生命哲学的认识。同年,另一件《转山》,包含了库布里克式的叙事结构与生命美学的时空感知。
幻象无不来往于现实,揉杂了幻想、自我、梦境,以螺旋上升的方式重复显现。
《转山》之后的十年,许仲敏步入幻象与感知的另一条路径,视线从单一的机械装置,转向含混的空间感知。像是电影蒙太奇的切换,旋转飞升的人物,在抽象的时空中开始与消失。顺时针转动的机械装置,风吹响的玻璃管,闪现的教堂,城外的废墟,散落在石块之间的小号与手风琴......艺术家创造了一个见所未见的奇景,展厅中的物像,漂浮于多重空间与纬度之中,像彼此具有了感官,一个活生生的世界,曾经来过,只留下稀少的信息。时空被给予距离。
象征总是具有两面性,勾连由物质和隐喻组成的双向世界。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,某个片刻或是破碎的场景,在我们的现实与幻想中曾经闪烁,它带着人的痕迹和体温,将我们引向所处的周遭,残酷的事实,一段溯往旅程:随处可见的工业废墟,大地的磅礴,霾光中的城市,曲折的河流,匆匆而过,涌动着无声欲望的人群,窗外,一束日光照入。
许仲敏借助光线、机械、声音和建筑的共同作用,将空间变化为一个现实和幻象叠加的感知体验。观众得以重新去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,它映射现实中的不堪与灾难,指向精神的无限,命运的不可抗拒。最终,留下一个深邃的目光,一首远去的挽歌。
或许,一个创造性的启示时刻,总能让我们感知到乾坤颠倒,或是别有洞天。重启的知觉,让我们获得某种想象,辨认什么是假象,什么是真实。它来源于人们所经历的过去与未来,在天堂与地狱间摆动,穿梭两极,既有西西弗斯式的悲剧理想,人存在的荒谬与无力;也有对此时此刻的感官礼赞,通向颂歌人的意志的诗篇,生与死,现实与轮回,平等与宿命,无奈与悲怆…..
1968年的法国五月运动达到高潮,人们失望、愤怒,以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来试图救赎,他们通过更具有反思性和前卫性的思想,渴望终结一个早已安排好的生存制度。在大洋的彼岸,垮掉的一代人,用堕落和精神的放逐,来发泄抵抗的无力,他们成日的嗑药、迷乱,罪恶的果实爆射出糜烂的欲望。1986年,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,同年,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。之后的数年中,客机坠毁,大坝崩塌,弥漫在全球的煤电开采,大规模的工业污染,亦如漂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雾霾,人们生活于此。
如今,在这个展厅中,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,太阳照常升起,生命永续轮回。
崔灿灿